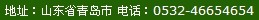|
从甘肃地区卫所的建置过程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庄浪卫设于洪武五年十一月,西宁卫设于六年正月,凉州卫设于九年(年)十月,永昌卫设于十五年(年)三月,镇番卫(今甘肃民勤)设于洪武中,山丹卫设于洪武二十三年(年)九月,甘州左卫设于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甘州右卫、甘州中卫设于二十五年三月,肃州卫设于二十七年十一月,甘州前卫、甘州后卫设于二十九年(年),镇夷守御千户所(今属甘肃高台)置于三十年(年)。[54]从以上诸卫设置时间来看,除镇番卫控制甘肃东北部,较为特殊外,其他卫所之设置呈现了由东至西、逐步设置的过程。这反映了洪武五年之后,明朝在甘肃的经略呈现了由东至西、逐步经略的过程。山丹以西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卫所设置尤其之晚,已经到了洪武后期,甚至末年。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在洪武五年便已设甘肃卫。“壬子,置甘肃卫都指挥使司、庄浪卫指挥使司。”[55]但此后该卫便默默无闻,《明太祖实录》仅再记其一次。“丙辰,升甘肃卫经历沈立本为户部侍郎。”[56]郭红认为甘肃卫于洪武二十四年废除,改置“甘州左卫”,所依据的史料是《明太祖实录》。[57]但该条史料原文为“置甘州左卫”,[58]并不及甘肃卫废除之事。从其他史籍的记载来看,似乎洪武晚期甘肃卫经历过一次重新设置。《大明一统志》载:“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肃卫。”[59]“本朝为甘肃卫,寻分置甘州左卫。”[60]而(万历)《肃镇志》却载:“(洪武)二十四年,设甘肃卫。二十五年,分设甘州左、右、中、前、后、中中六卫。”[61]《重刊甘镇志》亦载:“(洪武)二十四年,设甘肃卫。二十五年,分设甘州左、右、中、前、后、中中六卫。”[62]《读史方舆纪要》亦载甘肃卫设于洪武二十四年,洪武二十九年,改为甘州左卫,并设右、中、前、后等四卫。[63]如果甘肃卫经历过重新设置的推测属实的话,那么,甘肃卫在洪武九年之后,应经历过一次裁革。无论如何,甘肃卫的默默无闻已能说明洪武时期,明朝在甘肃西部的经略十分薄弱。正如郭红指出的那样,“(洪武)七年之前河西零星分布着庄浪、甘肃、西宁诸卫,相去甚远”,“当时(洪武十五年之前)凉州与甘州间的广阔地带内没有其他卫所,军事防御过于稀疏。”[64]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应与冯胜弃地有关。 洪武五年末甘肃并无军队驻防的情况同样也是可以印证《纪事录》的。洪武五年十二月,冯胜军自甘肃撤退后,邓愈(-年)受命征吐蕃,曾进军甘肃。 (朱元璋)遣(濮英)领西安、平凉、巩昌、临洮将士,往西海追朵只巴,出兰州,由大通河,直抵西宁铁佛寺。遣陕西行指挥使韦正,自归德州渡黄河,由巴亦咂沿西海边抵北而进。上命卫国公邓愈授以征西将军印,遣人赉制谕付愈,愈遣俞本赉制追英,督英与正合兵,凡六昼夜大雪,不及而归。[65] 由青海向北进军六昼夜,追击敌军,而未得见,可见洪武五年末,甘肃几为一个无人把守的军事真空地带。 最后,洪武五年明朝确实弃地宁夏的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俞本的记载。宣德年间,庆靖王朱?撰《宁夏志》,载“国朝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诏弃其地,徙其民于陕西。”[66]直倒洪武九年,“命长兴侯耿炳文弟耿忠为指挥,立宁夏卫,隶陕西都司,徙五方之人实之。后增宁夏前卫、宁夏左屯、右屯、中屯为五卫;寻并中屯于左、右二卫,为四卫。”[67]宁夏才开始逐渐经营。可见,冯胜确实在洪武五年放弃过甘肃等地,不过是在朱元璋授意之下,还是径自放弃,可以进一步探讨。目前来看,应是朱元璋授意。因为冯胜在弃地之后,并未受到惩罚。俞本记载此事时,可能出于对冯胜的厌恶,将此过失全部归罪于冯胜,并将洪武二十年冯胜辽东受罚之事移嫁于此事之上,以证冯胜之罪。 三“回鹘”名称的考证与洪武初年甘肃的地缘政治 冯胜弃地甘肃的原因是什么呢?《纪事录》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惧回鹘之兵”。“回鹘”,原称“回纥”,是隋唐时期活跃于西域的一支游牧民族。唐开成五年(年),回鹘可汗被杀,回鹘也分成四支外迁。年,随着高昌城毁于战火,高昌回鹘政权的灭亡,“回鹘”作为一个民族、政权,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但“回鹘”一词并未随之从历史中消失,不仅“回鹘文”仍在广大西域地区流行,而且惯常用典的元代汉族文人也仍然经常用“回鹘”指代畏兀儿与西域,以及用此称元朝境内的西域人,与“回回”一词经常混用。[68]俞本这里的“回鹘”所指代的是哪个政权或民族呢?《纪事录》共记载“回鹘”4次,除了此处外,其他3处为: (洪武元年八月)初三日,(徐)达、薛右丞(显)、参政傅友德领凤翔等五卫步军三万出虎北口追元君。初八日,至兴路,不获。元君行东路,友德军行西路,两路互差,但遇回鹘车辆人口,尽拘而回,获牛羊马匹十万。[69] (洪武元年十月),(徐达)至通州,内有回鹘欲作乱,事泄,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军士。[70] (洪武二十二年)甘肃、巴西、回鹘遣使赉表及金珠、玩(马戎)马、紫驼、结金珠、璎珞进贡。[71] 可见,俞本用“回鹘”,是取的元、明之际最广泛的涵义。冯胜所惧为西域的哪个政权与民族,从这里无法看出。但通过对西域地缘格局的揭示,可以找出这里“回鹘”所对应的政权。 成吉思汗(-年,-年在位)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依照蒙古部落分家产的习俗,将蒙古东部封于诸弟,称“东道诸王”。又将蒙古以西分封朮赤(-年)、窝阔台(-年,-年在位)、察合台(?-年)三子,称“西道诸王”。蒙哥汗时期,其弟旭烈兀(-年,-年在位)受封西域,也属西道诸王。西道诸王由于皆属黄金家族,相应具备继承汗位的资格,离心力较强,与中央不断产生摩擦,四大兀鲁思也逐渐发展为独立、半独立的四大汗国,自西向东依次为钦察(金帐)汗国、伊利(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本不与元朝接境,察合台兀鲁思最初受封地仅为天山一带的牧场,但阿鲁忽(?-约年)汗利用忽必烈(-年,-年在位)与阿里不哥(?-年)争夺汗位的时机,占领了阿姆河以北原属元朝直接管辖的城郭农耕地带,怯别汗趁窝阔台汗国海都(约-年,-年在位)去世,势力衰微之机,将其吞并,势力达到土鲁番。[72]元朝末年,当蒙古统治者面临长城以内汉族的叛乱时,察合台汗国黄金家族的统治也大为削弱,非黄金家族的“异密”们掌握了实权,察合台汗国从而分裂为西部的帖木儿帝国与东部的东察合台汗国。东部朵豁剌惕异密播鲁拥立秃黑鲁帖木儿(TuglugTemür,-年,-年在位)继承汗位,从而建立东察合台汗国(又称叶尔羌汗国,蒙兀儿斯坦,明人以其国都所在地称别失八里、亦力把里)。秃黑鲁帖木儿很有作为,宣布信仰伊斯兰教,从而稳固了社会基础,同时,逐渐削弱异密们的权力。在建立了强大的汗权之后,秃黑鲁帖木儿向西进攻河中地区,发动了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争。虽然占领了大片地区,但并未在当地建立长期而稳固的统治。秃黑鲁帖木儿也向东扩张势力,其势力威慑到了哈密,与元朝声气相接。[73]洪武初年,明朝尚未与帖木儿帝国及更西势力形成直接接触,明朝对西域的了解,恐怕更多是对邻国东察合台汗国的认知。故而,冯胜所惧“回鹘”势力,便应是东察合台汗国。那么,洪武初年东察合台汗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明朝建国的年,当东方汉地正处于元、明易代的大规模战争中时,察合台汗国境内也正展开着一场长达22年的内部战争。年,权力遭到削夺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哈马鲁丁趁也里亚思火者(īlyās-Khoja,?-年)汗去世的机会,大肆诛杀秃黑鲁帖木儿诸子,自立为汗,引起东察合台汗国部分势力的反对,帖木儿(-年,-年在位)趁机在年,对东察合台汗国发动进攻。而当明朝发动岭北之役的年,哈马鲁丁却向帖木儿帝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并占领了帖木儿帝国的大片领土,势头甚猛。[74]冯胜所面对的东察合台汗国,正处于此时势力大炽的时期。冯在岭北之役惨败的惊惧之下,对东察合台汗国东进甘肃心存畏惧,于是选择焚弃城池的弃地措施,以免贻粮于地的政策,也符合情理。傅友德占领瓜、沙二州后,之所以未进一步西进,也应在于避免与东察合台汗国发生战争。故而《纪事录》所载的“惧回鹘之兵”,便应是惧怕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 但冯胜撤兵之后,东察合台汗国并未东进,原因何在呢?这在于其与帖木儿帝国的长期内战使其无暇东进。东察合台汗国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向西进攻帖木儿帝国,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东察合台汗国与西部帖木儿帝国,本来同属一个国家——察合台汗国,哈马鲁丁以非黄金家族的身份篡夺汗位,不仅遭到了国内诸多政治势力的反对,而且帖木儿帝国标榜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也对哈马鲁丁的正统性构成了威胁,无论从统一察合台汗国的角度,还是从维护汗位的合法性角度,哈马鲁丁皆将西进河中,统一察合台汗国,剪除异己势力作为东察台汗国首要的战略目标。二,东察合台汗国以牧立国,自然条件较差,河中地区农耕条件十分优越,有以牧立国的东察合台汗国所不具备的丰富资源,占领河中地区对于东察合台汗国壮大经济实力,也很有帮助。故而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东察合台汗国首要的经略目标是河中地区,甘肃只是其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秃黑鲁帖木儿汗在位时,东察合台汗国势力才延展到嘉峪关以西的沙州、哈密地区。但也仅仅是渗透进来,主宰这一地区的仍是出伯系察合台后王集团。至于甘肃,更从未与察合台汗国产生过瓜葛。对于东察合台汗国来讲,这是一片陌生的东方地域。相应,哈马鲁丁只有在统一察合台汗国,消除后顾之忧后,才有可能考虑东进甘肃的问题。14世纪90年代,随着帖木儿击溃哈马鲁丁势力,秃黑鲁帖木儿幼子黑的儿火者继承东察合台汗国汗位,采取与帖木儿联姻和好的方式,消除了西部的威胁后,才开始经略东部地区,扣留明朝使者傅安,占领土鲁番,[75]进攻哈密。帖木儿帝国采取的战略选择也是首先消除直接竞争对手——察合台汗国的威胁,此后西进消灭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统一中亚、西亚地区后,才开始掉转方向,于永乐三年(年)发动了一场进攻明朝的战争,只是由于其突然身死,战争才戛然而止。[76]总之,无论东察合台汗国,还是帖木儿帝国,皆是建立于中亚的蒙古后裔政权,其首要的战略目标皆是确立汗位的正统性与剪除西域异己势力,而非进攻遥远的东方地区,甘肃只是其战略规划中的边缘地带。 岭北之役后,北元军队趁势南下,但对甘肃的进攻只局限在兰州、河州、会宁等甘肃东部靠近陕西的地方,[77]对甘肃广大地域并未见有收复举措。这同样在于北元以岭北行省东部与辽阳行省作为其统治的“心脏地带”,甘肃只是其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源于蒙元汗位之争引发的中央与西道诸王的重重矛盾。察合台后王虽一直未争夺汗位,但却多次卷入蒙古帝国汗位之争,且因疆域屡次扩张的关系,侵夺了元朝的利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西道诸王还包括受封岭北行省西部的诸王。蒙古帝国汗位世系从窝阔台系转至拖雷(-年)系后,窝阔台汗国与元朝中央关系不睦。窝阔台汗国后被察合台汗国所灭,余部东迁至岭北行省西部也儿的石河东北处,对元朝政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窝阔台后王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甚至在在至正二十年(年),发动叛乱,拥兵数十万,直逼中都,问责元顺帝(-,-年在位)。“‘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太半;若以国玺付我,我当自为之。’帝遣报之曰:‘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命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等将兵击之,不克,军士皆溃,秃坚帖木儿走上都。”[78]对北元构成最大威胁的来自拖雷系内部势力,即蒙哥(-年,-年在位)后裔与阿里不哥后裔。蒙哥去世后,忽必烈即位,蒙哥后裔自然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后裔更因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身死的缘故,与元中央结成世仇。蒙哥、阿里不哥后王封地皆在岭北行省西部,前者封地在札不罕河,后者封地在按台山至吉利吉思等处,[79]亦属西道诸王。可以讲,岭北行省西部甚至是北元的敌对地区,北元政权对岭北行省西部势力的担忧恐怕并不低于对明朝的程度,这也是元顺帝、昭宗爱猷识理达猎一直居于大漠东部,而不西进,甚至不愿向西北诸王求救的原因。元廷最初迁至上都后,御史徐敬熙请“征兵西北诸藩”,“上不之罪也”,并不采纳。[80]此后重臣再此奏请,仍不获允。“(知枢密院事)哈剌公尝太息,谓予曰:‘亡国之臣,岂可与图恢复?吾当与西北诸藩共图此事耳。’佶问何不早为此计,哈剌公曰:‘子独不见阿鲁辉王之事乎?’遂唏嘘而起。……(至正二十九年正月)初六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陈恢复大计,以兵力太弱,请征西北诸藩兵入援。疏入,寝不报,哈剌公之言,可谓先几矣。”[81]此后,顺帝甚至在臣僚屡屡提出西进建议的情况下,迟迟徘徊于上都、应昌二地,而不愿西进至蒙古帝国曾经的政治中心——和林,[82]原因也是和林距辽东远,而距西北诸王近的缘故。 东道诸王由于是成吉思汗诸弟,按照蒙古观念是无继承汗位的资格的,虽然在忽必烈时期曾联合海都,发动叛乱,但失败之后军队遭到重新分配,势力大损,已受岭北行省与辽阳行省的节制,[83]对中央的态度要更顺服一些,往往成为中央打击叛乱藩王的势力。[84]因此,辽阳行省与岭北行省东部一样,都是北元统治的大本营。甚至高丽境内之耽罗因是蒙古人聚居游牧之所,而成为顺帝王亡国前预先想好的避难之所。“时(己酉十八年,洪武二年,)王召元朝梓人元世于济州使营影殿世等十一人挈家而来。世言于宰辅曰:‘元皇帝好兴土木,以失民心,自知不能卒保四海,乃诏吾辈营宫殿耽罗,欲为避乱之计。功未讫而元亡,吾辈失衣食。……’”[85]可见北元政治中心之东移。顺帝北走,首先勤王的军队便是辽东之部也速不花与赛因帖木儿,左丞相失烈门卒于道路后,也速不花便充任左丞相,成为此时元廷的中坚力量。元廷迁至上都后,也赖辽东的供应,才立住脚跟。“十五日,车驾至上都,上都经红贼焚掠,公私埽地,宫殿官署皆焚毁,民居闲有存者。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公献币二万匹,粮五千石至,始有自存之势矣。”[86]顺帝去世之前,元廷所頼以保障者一直是也速不花,此人与明军多次作战。[87]而为世人所熟知的扩廓帖木儿此时一直未至元廷,更未起到保卫元廷的作用,只是在昭宗即位后,才扮演了北元中流砥柱的角色。洪武二十年,明军成功招降辽东木华黎(-年)后人纳哈出部,使北元汗廷失去了侧翼的保障,这才有了次年蓝玉(?-年)奇袭捕鱼儿海(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贝尔湖),北元汗脱古思帖木儿(-年,-年在位)无奈之下西进,却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所杀。[88] 相应,北元汗廷以岭北行省东部与辽阳行省作为统治的心脏地带,对于异己力量控制的西北地区,包括甘肃地区,视为边缘地带,无法顾及了。明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占领甘肃地区,恐怕与北元汗廷将军队集中于中、东二路,放弃西路有一定的关系。同样,明朝能在撤退甘肃之后,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再次收复甘肃,也得益于蒙古势力内部的纷争。正是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的势力均衡,以及北元、东察合台汗国皆以甘肃作为边缘地带的战略观念,也即洪武初年三方在甘肃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为明朝占领甘肃,确立西北疆界提供了条件。 四西北地区在明朝版图中的“边缘化”地位与明初的不征西域 但另一方面,如果说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在甘肃地区处于势力均衡的状态,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在14世纪90年代,东察合台汗国经过长期战争,受到帖木儿帝国的残酷打击,损失惨重,北元汗廷也被明军歼灭,明朝在形式上完成了肃清沙漠的伟业,三方均势的战略格局已被打破,呈现了明朝一支独大的局面。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下,明朝完全有条件利用察合台汗国内部战争的时机,如同汉唐那样,进军西域,实现对西域的直接控制。但明朝并未如此。另外,洪武十年(年),明军曾进至昆仑山,占领青海地区。“洪武九年丙辰(),五月,卫国公邓愈、西平侯沐英、南熊侯赵庸,上授以征西将军印剑,伐川藏,以都指挥韦正为前锋,直抵昆仑山,屠西番,获牛、羊、马匹数十万以归,遂于昆仑崖石间,刻‘征西将军邓愈总兵至此’绘其地里进上。”[89]山之背面即为东察合台汗国,当时西域战事正酬,明军也并未借机进一步西进,虽有山脉阻隔之缘故,但恐怕也与其无西进之心有关。明朝满足于与西域各国建立藩属关系,通过朝贡贸易维持双方的关系。[90]这其实延续了元朝与察合台汗国松散的关系形式。甚至在制御西域的方法上,明朝也呈现了继承元朝传统的特点,仍然以出伯系察合台后王控制沙州与哈密,牵制东察合台汗国,只是制度形式变成了羁縻卫所——关西七卫。 沙州、哈密是元甘肃行省最西端的两个地区,也是较为特殊的两个地区。忽必烈时期,察合台汗国内部由于争夺汗位的缘故,失利的出伯系察合台后王选择出走的方式,被元朝中央安置于沙州、哈密二地,借助其威望,以牵制察合台汗国,维持元朝西部边疆的安宁。最早注意到该地统治者与察合台家族关系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91]此后,日本学者陆续开展研究,其中以衫山正明的讨论较为深入。[92]胡小鹏对明初建立的关西七卫与出伯系察合台后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察合台汗国发生分裂,以出伯家族为首的部分察合台后王在元朝扶持下,形成了另一个察合台兀鲁思。直至明朝初年,这一察合台后王集团仍是嘉峪关外的实际统治者,明初的关西诸卫,主要是由该集团转化而来。诸卫之上还设有两个王号,目的是利用该集团察合台正统的政治资源,使西陲平稳过渡到明朝统治之下。”[93] 明朝继承元朝传统,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对嘉峪关以西的统治,虽然暂时行之有效,但由于这是以放弃对西域的积极经营为代价的,故而并不能根本性地解决西域问题。洪武、永乐年间,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便已开始经略东方。明中后期,虽然西域地区再次回归到政权林立的传统形态,无力发动对明朝的大举进攻,但却逐渐攻陷关西七卫,不仅使明朝无法控制西域事务,甚至西部防御也变得十分紧张。 明朝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但却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并未收复汉唐旧疆,而是满足于继承元朝旧疆,原因何在呢?这源于西北地区在明朝战略版图中处于边缘地带。明朝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起源于中南部,在东南部建立政权,统治者几乎皆来自中南方的的王朝,西北边疆远离明朝统治的心脏地带,只是一个边缘地带,明朝对西北地区,包括河西、西域不如建都关中的汉唐政权重视,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明末地理学家王士性指出:“前代都关中,则边备在萧关、玉门急,而渔阳、辽左为缓。本朝都燕,则边备在蓟门、宣府急,而甘、固、庄、凉为缓。”[94]毕竟古代国家经济、军事能力都十分有限,只能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战略重点地区。[95]西域之得失,尽管对西北边疆影响很大,但毕竟不如对汉唐政权影响之大。 洪武初年,西北地区的边缘地位尤其明显。中唐以来,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占领了原属汉族王朝统治的边疆地带,历经吐蕃、辽、金、西夏、蒙元政权的长期统治,长城沿线边疆地区的社会进程已纳入北族政权的脉络,在语言、宗教、文化、服饰等方面都呈现了“北方民族化”的特点。作为起源于东南中国的明政权,对新占领的西北地区存在疏远与隔膜,是十分正常的。冯胜在弃地甘肃之前,已经弃地河州(今甘肃临夏)了。通过《纪事录》的记载,我们能发现洪武初年政权内部对西北地区存在一定的疏远与隔膜态度。 大都督冯胜先于洪武二年四月克河州,以化外之地,不可守,将城楼库房屋尽行焚烧殆尽,拘虏南归。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至是愈复克之,韦正守其地,军士食苦薇,采木葺之,城楼仓库卫大门厅舍一新。[96] 冯胜放弃河州对当地造成的重大破坏可以通过次年宁正看到的情形看出来。“正初至河州,时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将士见之,咸欲弃去。”[97]此时俞本在宁正军中,以上情况,应为亲眼所见。 值得注意的是冯胜放弃河州的原因,“以化外之地,不可守”。河州属河湟流域,是中原王朝的传统统治地区,汉唐皆在此设置郡县,直接统治。但由于中唐以后为吐蕃所占,此后又先后经历了西夏、蒙元之占领,在元时是吐蕃等处宣慰司治所,是元朝统治甘青藏地区的政治中心,[98]元代包括河州在内的整个河湟地区是多民族杂居的区域。“元时的河湟地区是多民族的聚居区,除吐蕃、汉、蒙三大民族外,尚有来自中亚的色目人和少量的西夏人、金人。”[99]“藏化”、“党项化”、“蒙古化”的现象都较突出,在社会文化面貌上,与汉族已有很大的差别,是北方民族化的典型地区。冯胜看到河州社会文化面貌不类汉族,加以放弃,反映了南方汉人对西北北方民族化边疆地区的隔膜。 冯胜放弃河州也可以作为放弃甘肃的一个参照。河西地区同样经历了吐蕃、西夏、蒙元之占领,在藏化、党项化、蒙古化之外,甚至还经历了“伊斯兰化”的洗礼,对于冯胜来讲,可能更加隔膜。在当时客观形势下,加以放弃,也便符合他的心理了。故而,冯胜弃地甘肃,也有其主观上以甘肃为化外之地的观念的影响。《明太祖实录》载朱元璋对冯胜擅回行为进行了批评。 辛巳,征虏右副将军都督同知冯宗异等至京。初宗异守平凉,以关陕既平,胡虏畏服,不请于朝,辄引众还。及见,上诘之曰:“将军在平凉,外御胡虏,内镇抚关中,国家所托非轻也。乃不俟命,辄引众还。阃外之事将谁任之?”宗异顿首谢。上以其勋旧,姑置之。[] 《明史》载朱元璋对冯胜弃还进行了责罚。“(洪武二年)九月,帝召大将军还,命胜驻庆阳,节制诸军。胜以关、陕既定,辄引兵还。帝怒,切责之。念其功大,赦勿治。而赏赉金币,不能半大将军。”[]显示初洪武初年政权对北方民族化边疆地区仍是持收复态度的,但却取消甘肃行省的设置,将之纳入陕西的版图,这样,包括现在甘肃、宁夏在内的广大地域皆属陕西一省管辖,这相对于元朝,是一个倒退。这充分显示了朱元璋并不积极经营、大力巩固西北地区的态度。他所鍖椾含涓鐨偆鐥呭尰闄?鍏ㄥ浗娌荤枟鐧界櫆椋庢渶濂界殑鍖婚櫌
|
当前位置: 青川县 >洪武初年甘肃的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的形
时间:2017-9-14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quot阴平路quot改名由你说
- 下一篇文章: 紧急提醒广元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青川地灾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